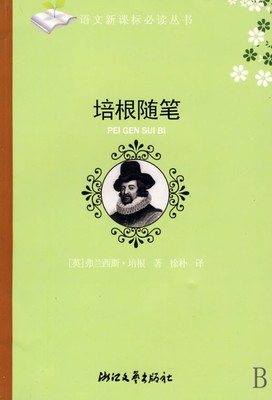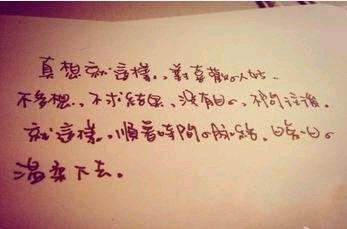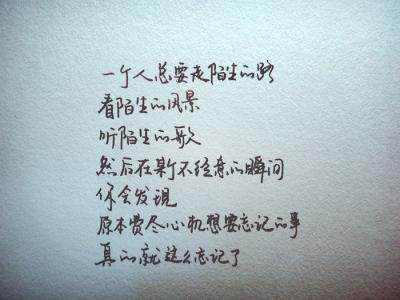每个人最初的相见都是偶遇,生活里忽然就冒出那么一个人,然后就再也没有走出去。
我始终记得,那是我十四岁的夏末,初中的最后一年,褪去了盛夏了燥热,有一份独属的芬芳,后来我想,那就是临近秋季时收获的味道吧。
那个转校生,本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随着父亲的工作迁徙,在五年后又回到最初的地方。
晨雾已尽数散去,阳光暖暖的洒下,门窗处看到阳光的舞步,肆意着,自由着,那时的我们最向往的就是名为自由的存在,不要父母的唠叨,老师的支配,觉得那时的生活,从闹钟把我们自被窝中拉起后就不再属于自己,洗漱,吃饭,出门,去学校,上课,下课,回家,只是按着制定好的章程。所以,晚到的那个男生身上,有着我所向往的自由,看到沐浴在阳光中的身影,我第一个想法是,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晚才来上课,记得,上学期,闹钟没电了,起来时已经晚了半个小时,紧赶慢赶在上课前赶到,被班主任训的好生狼狈。
然后,肆意的打了下那个男生,唇角是浅淡的笑意,在讲台停下,有一份自信弥漫,那一刻,我就明了他会在我们这个班活出色彩。他的书抱在胸前,第一排的我,清楚的看到他手指的廓型,瘦而纤长,男孩子极少有那么细致的手,想来是少做粗活的,转念一想,据说,他的父亲生意做得不错。
看了眼自己握笔的手,从来见了我的人都说我的手好看,十指纤纤,而我没什么概念,这一刻,在看到那个男生的手时忽然间发现,我的手真是好看的,同那个男生一般,多年后,我始终记得,曾经的我喜欢过一个男生,追想理由时,脑中冒出的是,那个男生的手好看得连女生都及不上。
我的眼光不错,他在短短的一年里,声名鹊起,不只是学习,同年级的都知道我们班有个清瘦好看的男生,似是晨雾里的朝阳,只那样看着就觉得满满的暖意。
因着座位的缘故,抑或是初识时那个意味不明的笑,没有丝毫的恶意,如划破乌云的暖阳。那个笑,让我觉得似曾相识,是的,那是最初的感觉,想想,或许是在他没转学的时候见过我,我从不否认自己的自信,在这个学校,我自认为,十个人里至少有八个是知道我的。
记得第二学期时,已然玩得很熟络。那时,没了冬季的冷寒,晨读时便没有戴手套,记得村里的老人说过,春季的晨风是凛冽的,于是我的手冻伤了,食指和小指最是严重,课间时,那人硬拉着我的手和他的比对,然后霸道的说是我传染给他的,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冻伤是可以传染的,我没打算给他什么面子,我知道的清楚,他的手是碰伤的,好几天后只剩下红红的一块,而那人却偏不,霸道任性的像孩子,根本不似往日桀骜不驯的少年。末了,回座位时说,虽然冻伤了有碍观瞻,但总体来说还算不错,跟我的手放一块也不至于像猪爪。
那就是我记忆中的人,连着阳光,鲜活的像是整个青春的色彩都倾倒在那年的岁月,这么多年,回想时,总是习惯性的闭上双眼,任满满的阳光洒落心间,然后看到他的笑容渐渐放大,直至连着脸容都消失不见,睁眼时,我的唇角多一份浅笑的弧,在心里道一声,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。
毕业的那个夏季,学校的槐花开得正盛,他说考完试后会来找我,我浅笑着说不用,从未想着他是专程来找我,据说他的目光在我好友身上久久停留,我不是愿意做踏脚石的人,骄傲的盛放着,尤其是在他的面前。
我终究是不知道他去找我没,考完试,我去了外地散心,回来时,我把最初的心动遗忘给了大海,而后几年,再也没聚到一起,不论是上学,还是同学聚会,那个夏天,似乎有我不知道的秘密,却再也不想过问,而我们,若有若无的联系着,然后,在值得祝福的节日送上寄语,记得要幸福,那么好的你。

偶然的遇见,然后是再也放不开的牵念,却大多不是以爱之名,越来越觉得,朋友是那般好的词汇。
 爱华网
爱华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