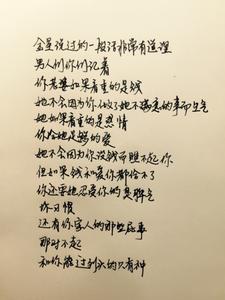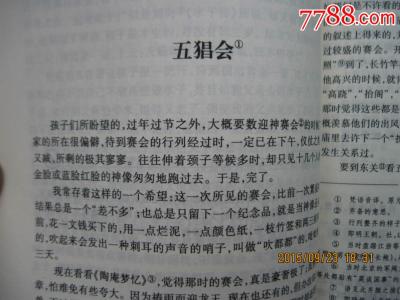每一个村庄的忧伤,都有一段难忘的往事,以及那些难忘的人;下面是有散文村庄忧伤,欢迎参阅。
散文村庄忧伤:村庄
每一个村庄,都有自身的气质,特点或者语言。
此时,已是深冬。此刻,已是深夜。深沉的慢慢长夜。在这个离故乡遥远的城市里,我,一个人,一台破电脑,空荡荡的房间,只有手指敲打键盘的声响陪伴着我。醒来,就再也睡不着。或许,是因为曾经沉睡过。
人一旦孤独寂寞、无奈,往往就会在意识里去反抗。用思念抵御。此刻,我想起了我的家乡,我住的村庄。
在大山深处,我的村庄,隐藏在树荫下。零星的点缀着那片山林。没有机器的轰鸣声,没有城里的纷争声。有的只是一份淡泊,一份宁静,自然纯朴。现在,我想村庄应该是一片银装素裹。最喜欢在这个时节,独自随意走走,留心看看。看看山,看看树,听听山风的嘶喊声,听听山涧泉水的叮咚声。
深冬,村庄是静谧的。偶尔打破这份静谧的除了枝桠上惊飞的麻雀,就只有牛圈里那头老黄牛的低哞声。麻雀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,这树已分不清是什么树,只是那些枝杈在寒风中还一直怒指着天空。一直就这么站着、指着。任凭风雪一层一层撕裂堆压,头一直昂着。老牛不时在牛圈里打转,草已枯黄,已被雪花覆盖。兴许,它的哞声在呼唤,或是在坚持等待中自励,期待春天的到来。或许,在它眼神里有一丝丝悲情,可目光一直默默的看着天与地相接的尽头。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嘴一直在细细轻轻的咀嚼,慢慢反刍。反刍着曾经的日日夜夜,反刍着曾经的滋味。快乐或是忧伤。
每次走向田野, 喜欢听,脚下雪花发出的沙沙声。随同我的脉搏一起跳跃。田间的路已没了踪迹,在雪下沉睡。其实,路在心中,已深深烙印。一同烙印的是那些行走在路上的这些风风雨雨。路始终总会醒来,引领着我们去寻找创造幸福、希望。田野也总会有那么些生机盎然的绿意,打破这寒冬的残虐,静静的微笑,静静的装扮这纯粹的白色世界。才发现,绿是如此的醒目,如此动人。
有人说,一个村庄有一把钥匙,只有这把钥匙才能打开村庄的门。我时时想起我的钥匙。烟筒底下的饭灶和烟筒上面渺渺炊烟就是我的钥匙。炊烟一直在飘起,冲向天空。连接炊烟的是灶台边我的母亲。养我长大的母亲。这个寒冬很冷,灶膛里的火花使得人无比温暖。火红在,炊烟在,母亲就在。母亲在那熟悉的饭菜味里,在那橘红色的火焰里。母亲老了矮了。在我一声声喊娘声中慢慢老了。是慈爱,是娘心,母亲把她的身高给了我,我长高了,母亲就矮了。被岁月的坎坷和磨难压矮的。一次次娘喊着我的乳名,用身体堵住四处漏风摇摇欲坠的家;一次次娘背着大大的背篓,用血换来我们成长的盛宴;一次次娘在屋檐底下,翘首盼望中更改了容颜。娘,您就是我回家的钥匙,一直贴肉的带着。我真想让您听见,我叫你的这声娘。每次回家,村东头的大树下都有您的身影。树叶黄了又绿,您呢!!!
村庄一直是这个村庄。厚重古朴,宁静悠长。一切都在改变,一切又都没改变。
树还是那些树,屋檐还是这个屋檐,路还是这条路,人还是那些人。只是有些人已沉睡在大山深处,我知道,他们一直依旧在。
村庄上的雪我想现在正在飘落,一片雪花覆盖着一片雪花,慢慢遮掩了村庄。村庄已没了吗?路呢?
问题是我问给自己的,答案呢?我想,天空里的炊烟知道。
散文村庄忧伤:村庄的美丽与忧伤
推开窗,便有微风扑面而来,像在冰水里浸过,清凉湿润直入肺腑,惊得每个细胞都激凌凌打个冷颤。
太阳初升,一副刚睡醒的样子,通红通红的脸,懒洋洋悬在两棵水杉树枝杈间,不言语,半边天空都被它的沉默憋红了。一些鸟从近处的这棵树飞到远处的那棵树,以极快的速度,只来得及看见几粒影子,鸣声响亮。一缕缕半透明的雾匍匐在地面,打算把成片的绿油菜、干枯的棉花梗、深耕过的黑土地藏住,像国画里的留白,有无限想像空间。远处的房屋和树木以雾为幕,半遮半掩,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,真怀疑一眨眼,它们就会消失。所有的物件表面都挂了一层薄霜,浅浅淡淡的白,和雾混在一起,苍茫,旷远。
出门,随意走一走。有雾,然而人进雾退,眼前的一切总是清晰的。
很静。听得见鸡的咕咕叫和拍打翅膀的声音,它们在菜园子周围转来转去,看似闲庭散步,其实是想趁人不备,钻过篱笆偷吃几口菜叶。菜都长得很肥,尤其是一身紫红衣裳的菜苔,一根一根,挺直粗壮,又鲜嫩多汁,看一眼就忍不住吞咽起口水。两只狗一前一后匆匆跑过,把鸡们吓得四散而逃。
村路上铺了水泥,路边有高高的水杉或白杨树,一棵挨一棵,依路形一直排向远方,在没有尽头的尽头聚成一个点。路很平展,走上去稳当舒适,心情也格外明媚,再不像早先的白土路,一到雨雪天就泥泞难行,才走出几步,鞋底就粘上厚厚的烂泥巴,沉得迈不动步。
屋后的排水沟,是连接长江的。以前,每个冬天,家家户户都要出人清理排水沟,除去杂草,挖出淤泥,保持水沟通畅。排洪、灌溉、饮用、洗涤,都是靠沟里的水。沟两边长满依依杨柳,水清澈透明,从长江游来的鱼肥美新鲜。孩子们可以在水里游泳、嬉戏、抓鱼。大人从里面挑水做饭、洗衣、洗菜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,顾不上清理排水沟,排水沟虽然还起着早先的功用,却越来越不通畅,越来越脏。前两年,村里装了自来水,这排水沟也就难得再有人光顾,连那些极副水乡特色的跳板,也都了无踪迹。如今,它已经苍老疲惫得不成样子,杂草、稻草、枯树枝横陈其中,仅有的少量水面也浮了一层绿藻,那绿藻绿得娇嫩可爱,却让人心生孤独与凄凉。
太阳升高了些,醒了瞌睡,光芒也有了力量,雾气和薄霜,在这样的光芒里慢慢消散于无形。天地之间,刹那间清朗起来,人站在旷野中,自感渺小如沙尘,深深吸一口变温润了的纯净空气,想高声喊一嗓子,却又嗫嗫地,突然失了勇气,只好拿眼去细看远远近近的庄稼地。
豌豆苗高已过尺,油菜苗挨挨挤挤,几乎看不见地面,也有性子急的,长出了花骨朵。一些棉田深翻过了,露出黑色松散的土壤,能感觉到里面蕴藏的养育新生命的力量。也有的还留着棉梗,没有风,它们一动不动,直楞楞站着,脚边是生机盎然的腊菜,一行一行,绿得耀眼。

田间小径细细长长,像人心里那条通向故乡的路,无论什么时候,都不会荒芜。是的啊,不会荒芜,你看,路边的枯草丛里露出蒲公英含笑的脸,柠檬黄,娇艳妩媚。
在这样一个早春的清晨,谁看见村庄的美丽与忧伤?
我以游子的身份站在棉花田里,沉默不语,一低头,棉花都开了。
散文村庄忧伤:感受乡村
有一种声音夹杂着水汽,携着朦胧的月色,穿过仿佛是铁的踊跃的兽脊似的,漆黑的起伏的连山,远远地跑过来,我只记得,依稀的记得,大抵是这样的……
“雪花纷飞雪珠跳,头重脚轻身打飘……少年不识愁滋味,猛然回首冷汗浇。携妓而归天下耻,门庭名声一旦抛。莫如就让与那孙富……错错错啊。。此行径无异于纨绔与恶少……”
青衣风头绣鞋,绿裙衩里露出的红里子;花旦的兰花指、甩水袖、水上飘样的小碎步,以及,不瘟不火、缠绵悱恻的唱腔……这便是乡村的戏。
大夏天儿的,大冷天儿的,又或者一年里特定的几个月份,乡村的小戏便不绝于耳,总觉着,这咿咿呀呀不知所云的戏词没有任何看头,临时搭建的戏台旁的扩音喇叭朝天的刺耳,对戏的认识也只局限于有看头的变脸之流。我也曾赶过一场小戏,五六岁的年纪,看着小生浓墨重彩的美,心底唏嘘了几番,不喜老旦,丑角,只喜那青衣小生与花旦,那时年少,瞪着眼睛楞是聚精会神的听了会儿,也终于孩子心性,受不住困了,也不记得是怎样散了场,怎样的喧嚣空白成了寂静,那时心心念念要见小生一面的念头现在想来也忍俊不禁。
后来,也曾去戏园里
 爱华网
爱华网